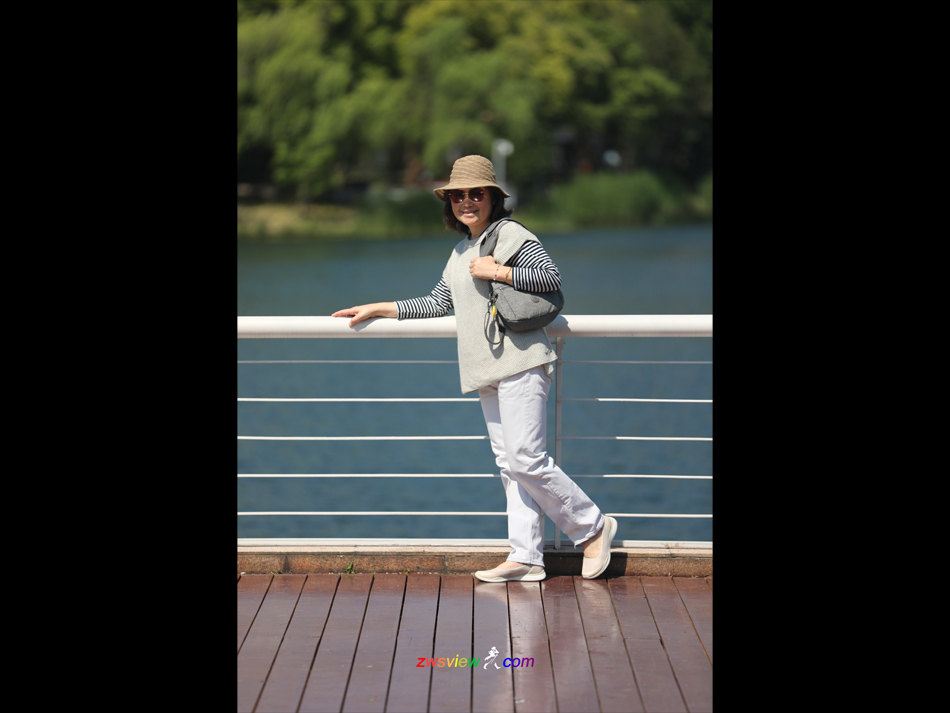《小巷》F0300000619 · 2024年5月13日摄于 中国上海青浦金泽古镇
五点起床,六点出门,七点抵达离家约75公里的金泽古镇。
江南水乡的格局都差不多,无非就是小桥流水、枕河人家。只是金泽的河网尤其的密,桥也就尤其的多。「出门即过桥,人家尽枕河」是对金泽最贴切的描述。
据说,金泽原有六观、一塔、十三坊、四十二虹桥。
桥,是金泽的最大看点。金泽人对桥似乎赋予了某种特殊的精神寄托。在金泽,「庙庙有桥,桥桥有庙」,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尽管现在很多依桥而立的寺庙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在金泽人的心中,它们依然都还在的。我们用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兜兜转转、寻寻觅觅,把万安桥、如意桥、普济桥、迎祥桥、放生桥、林老桥、天皇阁桥这七座现在的自宋至清的古桥逛了个遍,发现好几座古桥的桥堍依旧香火不断。

《鲜肉小笼包》B0000000610 · 2024年4月3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苏小柳手工点心五角场分院
《汤包》
梁实秋
说起玉华台,这个馆子来头不小,是东堂子胡同杨家的厨子出来经营掌勺。他的手艺高强,名作很多,所做的汤包,是故都的独门绝活。
包子算得什么,何地无之?但是风味各有不同。上海沈大成、北万馨、五芳斋所供应的早点汤包,是令人难忘的一种。
包子小,小到只好一口一个,但是每个都包得俏式,小蒸茏里垫着松针(可惜松针时常是用得太久了一些),有卖相。名为汤包,实际上包子里面并没有多少汤汁,倒是外附一碗清汤,表面上浮着七条八条的蛋皮丝,有人把包子丢在汤里再吃,成为名副其实的汤包了。这种小汤包馅子固然不恶,妙处却在包子皮,半发半不发,薄厚适度,制作上颇有技巧,台北也有人仿制上海式的汤包,得其仿佛,已经很难得了。
天津包子也是远近驰名的,尤其是苟不理的字号十分响亮。其实不一定要到苟不理去,搭平津火车一到天津西站就有一群贩卖包子的高举笼屉到车窗前,伸胳膊就可以买几个包子。包子是扁扁的,里面确有比一般为多的汤汁,汤汁中有几块碎肉葱花。有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才出笼的,包子里的汤汁曾有烫了脊背的故事,因为包子咬破,汤汁外溢,流到手掌上,一举手乃顺着胳膊流到脊背。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不过天津包子确是汤汁多,吃的时候要小心,不烫到自己的脊背,至少可以溅到同桌食客的脸上。相传的一个笑话:两个不相识的人据一张桌子吃包子,其中一位一口咬下去,包子里的一股汤汁直飚过去,把对面客人喷了个满脸花。肇事的这一位并未觉察,低头猛吃。对面那一位很沉得住气,不动声色。堂倌在一旁看不下去,赶快拧了一个热手巾把送了过去,客徐曰:「不忙,他还有两个包子没吃完哩。」
玉华台的汤包才是真正的含着一汪子汤。一笼屉里放七八个包子,连笼屉上桌,热气腾腾,包子底下垫着一块蒸笼布,包子扁扁的塌在蒸笼布上。取食的时候要眼明手快,抓住包子的皱褶处猛然提起,包子皮骤然下坠,像是被婴儿吮瘪了的乳房一样,趁包子没有破裂赶快放进自已的碟中,轻轻咬破包子皮,把其中的汤汁吸饮下肚,然后再吃包子的空皮。没有经验的人,看着笼里的包子,又怕烫手,又怕弄破包子皮,犹犹豫豫,结果大概是皮破汤流,一塌糊涂。有时候堂倌代为抓取。
其实吃这种包子,其乐趣一大部分就在那一抓一吸之间。包子皮是烫面的,比烫面饺的面还要稍硬一点,否则包不住汤。那汤原是肉汁冻子,打进肉皮一起煮成的,所以才能凝结成为包子馅。汤里面可以看得见一些碎肉渣子。这样的汤味道不会太好。我不太懂,要喝汤为什么一定要灌在包子里然后再喝。

《乳鸽》B0000000606 · 2024年4月29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匠心小厨悠方店
烤乳鸽,最初的源头是太平馆的红烧乳鸽,一道在二十五分钟之内完成卤汁、生炸、上桌的西菜。对的,这是一道西菜,而非粤菜,因为太平馆是一家中国人创办的西餐馆,创办人叫徐老高,之前曾在洋行帮厨,对西菜有一定的了解。
民国十二年,《民国日报》报道了一则新闻,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广州宴请高级将领享用太平馆的红烧乳鸽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孙中山说,他之所以来广州,是继续革命的未竟之业。第一步,「要使人人有饭喫」;第二步,「更要使人人都有好饭好菜吃」。但不能止步于此,「一定要更进一步,解救被残暴军阀欺凌压榨的全国同胞,让四万万同胞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鸽子」。孙中山认为,「这才是革命最大的目的、最终的目标!」

《拆骨肉炖酸菜》B0000000605 · 2024年4月6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冰城老于家国和路店
几年前,雪村的一首洗脑神曲《东北人都是活雷峰》风靡大江南北,其中有一句歌词「翠花,上酸菜」无意间带火了东北人家餐桌上的当家花旦酸菜。
过去的东北,由于天寒地冻,每到冬季,当地既种不了叶菜,外面的叶菜也运不进来。为了在冬季能吃上叶菜,入冬前,家家户户都会贮存好几百斤大白菜,也就是所谓的「冬贮大白菜」。
大白菜的贮存通常有两种法子:窑藏和腌渍。后者,用东北人的话说,叫「渍酸菜」。这里的「渍」读作「积」。
关于如何渍酸菜,清朝文人徐宗亮在《黑龙江纪略》中有很详细的描述:「至秋末则惟黄芽白一种,土人以盐水浸之,储藏瓮中留冬春之需,谓之酸菜。」「黄芽白」指大白菜。上海人管大白菜叫「黄芽菜」。
渍酸菜,是一个发酵过程,期间会产生大量的乳酸菌。渍过的大白菜因此也就变成了酸菜。
在东北,酸菜有很多种吃法,可炖,可炒,可煮,也可以做成酸菜馅,比如酸菜炖白肉和酸菜饺子,极美味。

《辣肉麺》B0000000604 · 2024年4月5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浣纱制麵局
四千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在吃麺了。
二零零二年,考古工作者在喇家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保存完好的陶器,其中有一件篮纹红陶碗,略为倾斜地翻扣在地面上。当陶碗被提取后,人们发现陶碗下面的地面上残留有一堆碗状遗物,下层泥土,而和碗底接触的部位却呈现出清晰的麺条状结构。这些麺条状的物体粗细均匀,卷曲缠绕在一起,而且鲜有断头,其直径大约为0.3厘米,总长度不短于50厘米,呈纯正的米黄色。经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检测,认定陶碗中的遗物为麺条。后又经进一步成分分析,这些麺条的原料为大量的粟与少量的黍。除此之外,成分中还包括少量的油脂、类似藜科植物的植硅体以及少量动物的骨头碎片。
由此推断,这很可能是一碗四千多年前的「浇头麺」。

《桂花香烤鸭》B0000000602 · 2024年4月19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青年公社创智天地店
梁实秋曾写过一篇散文,说的是北京烤鸭,题目叫《烧鸭》。传统上,北京人管烤鸭叫烧鸭,因为「烤」这个字是不久前才有的,以前根本没有。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烤」这个字,为齐白石所创。北京有个很有名气的烤肉铺,叫「烤肉宛」。齐白石曾为烤肉宛题过一小匾:「清真烤肉宛」,并注「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香港作家董桥曾出过一本书,谈及过此事。此书的名字叫《文字是肉做的》,颇为有趣。
作家、美食家汪曾祺曾见到过齐白石的题匾。他在散文《帖秋膘》有这样一段文字:「『烤肉宛』原来有齐白石写的一块小匾,写得明白:『清真烤肉宛』,这块匾是写在宣纸上的,嵌在镜框里,字写得很好,后面还加了两行注脚:『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并说:「我曾写信问过语言文字学家朱德熙,是不是古代没有『烤』字,德熙复信说古代字书上确实没有这个字。看来『烤』字是近代人造出来的字了。」
汪曾祺还曾请现在杂谈文家邓拓写文专门谈谈诸书到底有没有「烤」字。朱德熙、汪曾祺和邓拓三位学者的观点比较统一,认为「烤」字或从「燺」字而来,又作「熇」。燺是多音字,做动词时读「烤」。
不过,也有学者考证过此事,答案是「烤」字至迟在明时就已出现,比如《金瓶梅》和《红楼梦》中就有「烤」字。
我觉得,像齐白石、汪曾祺、朱德熙、邓拓、董桥这样的大家均遗漏了《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烤」字,这个很难想像。
不管齐白石之前有没有「烤」字,我很好奇的一点是,在齐白石题「清真烤肉宛」匾之前,「烤肉宛」叫什么。

《一杯美式咖啡》B0000000600 · 2024年4月15日摄于中国上海宝山Monoto Coffee芳草寓店
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我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脑雾」。
后疫情时期,很多人感觉和疫情前比,自己的思维或反应迟钝、模糊、混乱、健忘,以及失语、注意力不集中。简而言之,诸事一头雾水。有科学家称这类现象为「脑雾」,归为「长新冠」,即可能的新冠后遗症诸多症状之一。
医学上,「脑雾」并非是一个专业术语,上述有关脑雾的一系列现象也算不上是「症状」,只是一些主观感觉的描述。但「脑雾」现象确实存在,而且远在疫情前就已受到科学家们的关注。
有专家认为,脑雾很可能和炎症、慢性病以及受病毒感染而导致的免疫力下降有关。这可以部分解释长新冠中脑雾现象明显增多的状况。
目前,脑雾没有特效药物或疗法,但一些专家认为: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对改善脑雾有积极作用。

《乳鸽》B0000000598 · 2024年4月29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匠心小厨悠方店
《鸽》
梁实秋
明陶宗仪《辍耕录》:「颜清甫曲阜人,尝卧病,其幼子偶弹得一鹁鸽,归以供膳。」用弹弓打鸽子,在北方是常有的事。打下来就吃掉它。颜家小子打下的鸽子是一只传书鸽,这情形就尴尬了,害得颜老先生专诚到传书人家去道歉。
我小时候家里就有发射泥丸的弓弩大小二只,专用以打房脊上落着的乌鸦,嫌它呱呱叫不吉利,可是从来没打中过一只。鸽子更是没有打过。鸽子的样子怪可爱的,在天空打旋尤为美观,我们也没想过吃它的肉。有许多的人家养鸽子,不拘品种,只图其肥,视为家禽的一种。我不觉得它的肉有什么特别诱人处。
吃鸽子的风气大概是以广东为最盛。烧烤店里常挂着一排排的烤鸽子。酒席里的油淋乳鸽,湘菜馆里也常见。乳鸽取其小而嫩。连头带脚一起弄熟了端上桌,有人专吃它胸脯一块肉,也有人爱嚼整个的小脑袋瓜,嚼得喀吱喀吱响。台北开设过一家专卖乳鸽的餐馆,大登广告,不久就关张了,可见嗜油淋乳鸽者不多。
炒鸽松比较的还可以吃,因为鸽肉已经切碎,杂以一些佐料,再有一块莴苣叶包卷起来,吃不出什么鸽肉的味道。就像吃果子狸,也吃不出什么特别味道,直到看见有人从汤里捞出一个龇牙咧嘴的脑壳,才晓得是吃了果子狸。
北方馆子有红烧鸽蛋一味。鸽蛋比鹌鹑蛋略大,其蛋白蛋黄比鹌鹑蛋嫩,比鸡蛋也嫩得多。先煮熟,剥壳,下油锅炸,炸得外皮焦黄起皱,再回锅煎焖,投下冬菇笋片火腿之类的佐料,勾芡起锅,好几道手续,相当麻烦。可是蛋白微微透明,蛋不大不小,正好一口一个,滋味不错。有人任性,曾一口气连吃了三盘!

《招牌地狱火叉烧麺》B0000000599 · 2024年4月17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一楽日式拉麺
在日本,拉麺的流派非常多,但通常认为,大致可分为三大流派:北海道札幌的味噌拉麺、九州博多的豚骨拉麺以及福岛喜多方的酱油拉麺。
札幌拉麺的特色是以味噌、猪油和蒜泥调味的汤底,香气浓郁。知道札幌人对拉麺有多爱吗?一座人口不足两百万的城市开了七百多家拉麺店,平均两千多人就有一家拉麺店,令人咋舌。
博多拉麺的特色是用猪腿骨经十几个小时文火慢熬而成的汤底,且浓且白,肉香扑鼻。博多就是福冈。当初两座城市合并时,「福冈」一名仅以一票的优势得以保留,但时至今日,这座城市的港口及车站仍以「博多」命名。大名鼎鼎的「一蘭」和「一風堂」是博多拉麺的两张名片。
喜多方位于福岛,传统上以酿造见长,出产优质的酱油、味噌和酒。喜多方的酱油拉麺的特点是用当地出产的酱油调味。尽管也是采用豚骨和小鱼干熬制汤底,但与札幌的味噌拉麺、博多的豚骨拉麺这二者的汤底相比,喜多方酱油拉麺的汤底要清淡得多,浇头也相对简单,通常只是叉烧片和大葱圈。喜多方是一个人口仅五万的小城,据说拉麺店有一百二十家。也难怪喜多方的拉麺如此出名。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做不出极致品质的拉麺,想生存,几无可能。

《文火雪花牛肉》B0000000597 · 2024年3月17日摄于中国上海宝山浙东头
《牛肉》
汪曾祺
我一辈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
昆明的牛肉馆的特别处是只卖牛肉一样,外带米饭、酒,不卖别的菜肴。这样的牛肉馆,据我所知,有三家。有一家在大西门外凤翥街,因为离西南联大很近,我们常去。我是由这家「学会」吃牛肉的。一家在小东门。而以小西门外马家牛肉馆为最大。楼上楼下,几十张桌子。牛肉馆的牛肉是分门别类地卖的。最常见的是汤片和冷片。白牛肉切薄片,浇滚烫的清汤,为汤片。冷片也是同样旋切的薄片,但整齐地码在盘子里,蘸甜酱油吃,(甜酱油为昆明所特有)。
汤片、冷片皆极酥软,而不散碎。听说切汤片冷片的肉是整个一边牛蒸熟了的,我有点不相信:哪里有这样大的蒸笼,这样大的锅呢?但切片的牛肉确是很大的大块的。牛肉这样酥软,火候是要很足。有人告诉我,得蒸(或煮?)一整夜。其次是「红烧」。「红烧」不是别的地方加了酱油闷煮的红烧牛肉,也是清汤的,不过大概牛肉曾用红粬染过,故肉呈胭脂红色。「红烧」是切成小块的。这不用牛身的「好」肉,如胸肉腿肉,带一些「筋头巴脑」,和汤、冷片相较,别是一种滋味。还有几种牛身上的特别部位,也分开卖。却都有代用的别名,不「会」吃的人听不懂,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如牛肚叫「领肝」;牛舌叫「撩青」。
很多地方卖舌头都讳言「舌」字,因为「舌」与「蚀」同音。无锡陆稿荐卖猪舌改叫「赚头」。广东饭馆把牛舌叫「牛脷」其实本是「牛利」,只是加了一个肉月偏旁,以示这是肉食。这都是反「蚀」之意而用之,讨个吉利。把舌头叫成「撩青」,别处没有听说过。稍想一下,是有道理的。牛吃青草,都是用舌头撩进嘴里的。这一别称很形象,但是太费解了。牛肉馆还有牛大筋卖。我有一次同一个女同学去吃马家牛肉馆,她问我:「这是什么?」我实在不好回答。我在昆明吃过不少次牛大筋,只是因为它好吃,不是为了壮阳。「领肝」、「撩青」、「大筋」都是带汤的。牛肉馆不卖炒菜。上牛肉馆其实主要是来喝汤的,汤好。
昆明牛肉馆用的牛都是小黄牛,老牛、废牛是不用的。
吃一次牛肉馆是花不了多少钱的,比一般小饭馆便宜,也好吃,实惠。
马家牛肉馆常有人托一搪瓷茶盘来卖小菜,蕌头、腌蒜、腌姜、糟辣椒,有七八样。两三分钱即可买一小碟,极开胃。
马家牛肉店不知还有没有?如果没有了,就太可惜了。
昆明还有牛干巴,乃将牛肉切成长条,腌制晾干。小饭馆有炒牛干巴卖。这东西据说生吃也行。马锅头上路,总要带牛干巴,用刀削成薄片,酒饭均宜。

《日式拉麺》B0000000596 · 2023年11月18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麺屋庄野悠方店
《笋》
梁实秋
我们中国人好吃竹笋。《诗经 · 大雅 · 韩奕》:「其簌维何,维笋维蒲。」可见自古以来,就视竹笋为上好的蔬菜。唐朝还有专员管理植竹,唐书百官志:「司竹监掌植竹苇,岁以笋供尚食。」到了宋朝的苏东坡,初到黄州立刻就吟出「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之句,后来传诵一时的「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笋煮肉。」更是明白表示笋是餐餐所不可少的。不但人爱吃笋,熊猫也非吃竹枝竹叶不可,竹林若是开了花,熊猫如不迁徙便会饿死。
笋,竹萌也。竹类非一,生笋的季节亦异,所以笋也有不同种类。苦竹之笋当然味苦,但是苦的程度不同。太苦的笋难以入口,微苦则亦别有风味,如食苦瓜、苦菜、苦酒,并不嫌其味苦。苦笋先煮一过,可以稍减苦味。苏东坡吃笋专家,他不排斥苦笋,有句云:「久抛松菊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他对苦笋还念念不忘呢。黄鲁直曾调侃他:「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春衫诚可脱。」为了吃苦笋,连官都可以不做。我们在台湾夏季所吃到的鲜笋,非常脆嫩,有时候不善挑选的人也会买到微苦味的。好像从笋的外表形状就可以知道其是否苦笋。
春笋不但细嫩清脆,而且样子也漂亮。细细长长的,洁白光润,没有一点瑕疵。春雨之后,竹笋骤发,水分充足,纤维特细。古人形容妇女手指之美常曰春笋。「秋波浅浅银灯下,春笋纤纤玉镜前。」(《剪灯余话》)。这比喻不算夸张,你若是没见过春笋一般的手指,那是你所见不广。春笋怎样做都好,煎炒煨炖,无不佳妙。油闷笋非春笋不可,而春笋季节不长,故罐头油闷笋一向颇受欢迎,惟近制多粗制滥造耳。
冬笋最美。杜甫发秦州:「密竹复冬笋」,好像是他一路挖冬笋吃。冬笋不生在地面,冬天是藏在土里,需要掘出来。因其深藏不露,所以质地细密。北方竹子少,冬笋是外来的,相当贵重。在北平馆子里叫一盘「炒二冬」(冬笋冬菇)就算是好菜。东兴楼的「虾子烧冬笋」,春华楼的「火腿煨冬笋」,都是名菜。过年的时候,若是以一蒲包的冬笋一蒲包的黄瓜送人,这份礼不轻,而且也投老饕之所好。我从小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冬笋炒肉丝,加一点韭黄木耳,临起锅浇一勺绍兴酒,认为那是无上妙品,但是一定要我母亲亲自掌勺。
笋尖也是好东西,杭州的最好。在北平有时候深巷里发出跑单帮的杭州来的小贩叫卖声,他背负大竹筐,有小竹篓的笋尖兜售。他的笋尖是比较新鲜的,所以还有些软。肉丝炒笋尖很有味,羼在素什锦或烤麸之类里面也好,甚至以笋尖烧豆腐也别有风味。笋尖之外还有所谓「素火腿」者,是大片的制炼过的干笋,黑黑的,可以当做零食啃。
究竟笋是越鲜越好。有一年我随舅氏游西湖,在灵隐寺前面的一家餐馆进膳,是素菜馆,但是一盘冬菇烧笋真是做得出神入化,主要的是因为笋新鲜。前些年一位朋友避暑上狮头山住最高处一尼庵,贻书给我说:「山居多佳趣,每日素斋有新砍之笋,味绝鲜美,盍来共尝?」我没去,至今引以为憾。
关于冬笋,台南陆国基先生赐书有所补正,他说:「『冬笋不生在地面,冬天是藏在土里』这两句话若改作『冬笋是生长在土里』,较为简明。兹将冬笋生长过程略述于后。我们常吃的冬笋为孟宗竹笋(台湾建屋搭鹰架用竹),是笋中较好吃的一种,隔年秋初,从地下茎上发芽,慢慢生长,至冬天已可挖吃。竹的地下茎,在土中深浅不一,离地面约十公分所生竹笋,其尖(芽)端已露出土壤,笋箨呈青绿。离地表面约尺许所生竹笋,冬天尚未露出土表,观土面隆起,布有新细缝者,即为竹笋所在。用锄挖出,笋箨淡黄。若离地面一尺以下所生竹笋,地面表无迹象,殊难找着。要是掘笋老手,观竹枝开展,则知地下茎方向,亦可挖到竹笋。至春暖花开,雨水充足,深土中竹笋迅速伸出地面,即称春笋。实际冬笋春笋原为一物,只是出土有先后,季节不同。所有竹笋未出地面都较好吃,非独孟宗竹为然。」附此志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