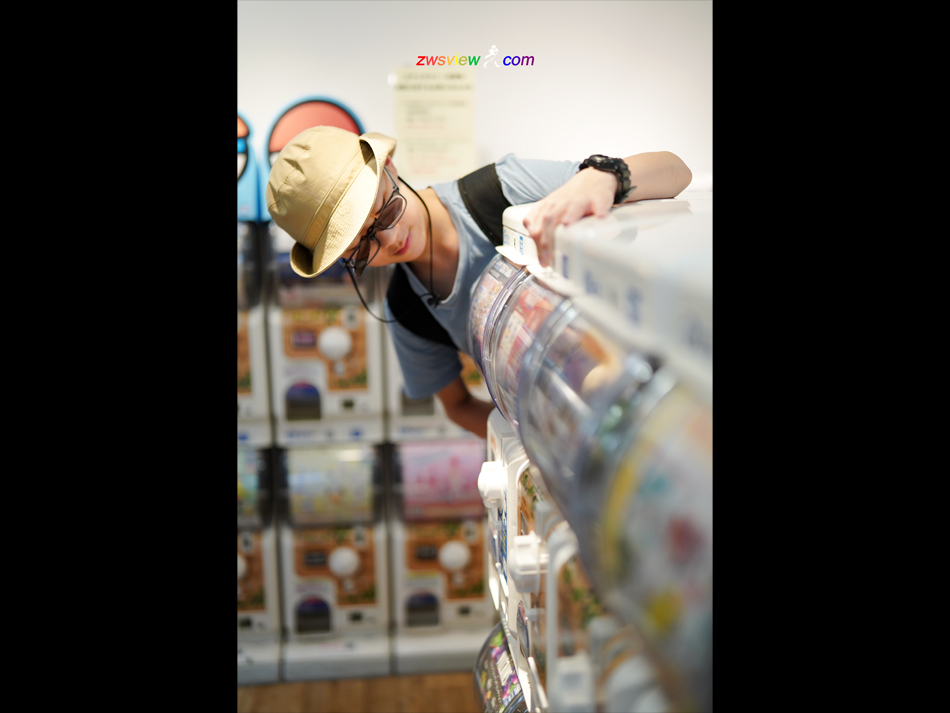《片鸭》F0200000070 · 2024年8月3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小吊梨汤五角场万达店
中国的很多地方有中秋吃鸭子的习俗。追溯这一习俗的来源,各地有各地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最流行的,是说元朝时汉人不满蒙古人的统治,特意相约在中秋这天一起吃鸭子。那时的汉人管蒙古人叫「鞑子」,和「鸭子」音近。但这种说法过于牵强,能在民间广泛流传,估计也就是汉人能私底精神胜利一下,仅此而已。
其实,中秋节吃鸭子,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时节的鸭子在一年中最肥美。
鸭子在被人类驯化前是候鸟,每年的秋天都要去南方越冬。迁徙前的鸭子必须养得膘肥体壮才能应对接下来的长途飞行。
中秋节上海人一道传统菜:鸭子芋艿汤,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中秋时节不光鸭子肥美,芋艿也正当令。鸭子配芋艿,再自然不过了。再有,旧时文人好中秋把酒持螯,不正是因为入秋后的螃蟹黄正满、膏正肥嘛。
倘若传说,蒙古人不入关,汉人难不成中秋还不吃鸭子了么。

《小吊梨汤》B0000000663 · 2024年8月3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小吊梨汤五角场万达店
小吊梨汤,用雪花梨、冰糖、银耳、话梅等熬煮而成的热饮,是老北京的传统吃食。
「小吊梨汤」一名的由来,众说纷纭。最多的,是说因为过去常用铜「提吊」来作为量器。这种说法听上去多少有些牵强。
我倒是觉得,所谓小吊梨汤,就是用小铜壶熬煮的梨汤。很多地方都管烧水用的壶叫吊子,包括上海。上海人管烧水壶叫「铜吊」。
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
老北京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在老东安市场北门一狭长甬道的一头,常有一大爷推着小车卖梨汤。小车上放着两只煤球炉子,煤球里插着几个小吊子用来熬梨汤。这一场景为很多老北京所熟知。
很可能,大爷用小吊子熬煮出来的梨汤比其他大锅熬煮的梨汤更具风味,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只要是梨汤都称「小吊梨汤」,有点凡糖炒栗子必是「良乡」的意思。

《净手》F0300000647 · 2024年7月28日摄于日本熊本水前寺成趣园
成趣园位于熊本城东南,由熊本藩第一代细川氏藩主的细川忠利于17世纪30年代创建。最初,这里仅有一寺,即水前寺,以及一间茶室,后扩建成桃山式庭园成趣园。
这是一座围绕池塘而建的回游式庭园,池塘引入的是阿苏山的泉水,庭园之名取自中国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的「园日涉以成趣」。入口处有两座可以追溯到明治时代的石桥。东面的湖对岸有一座人工山「筑山」,左右对称的山形非常醒目,令人联想起富士山。庭园北面是出水神社,于1878年建成,而就在前一年,由萨摩,即今鹿儿岛县武士向明治政府发起叛乱而导致的「西南战争」爆发,熊本市大片地区都毁于这场战火。传说,叛军进攻时在庭园内的这座微型富士山上部署了火炮。又据传,这里的松树是由细川忠利栽培的盆景培育而成。继续往前走一段,就是拥有朱红色鸟居的稻荷神社,里面供奉着丰收之神。早春时节,神社附近的四棵梅树花繁艳丽。
沿着庭园的东端是一条铺满碎石的笔直大道,自1878年出水神社建成以来,在这条路上举行的「流镝马」,即在飞奔的马背上射响箭比赛,一直是神社春祭和秋祭的一部分。细川家族是日本「武田流」流镝马的代表,不过现在这项表演更像是宗教仪式而非武术。沿着这条大道,可以看到「肥后六花」中的五种:肥后山茶花、肥后茶梅、肥后芍药、肥后菊和肥后花菖蒲。在大道南端,有一个展示细川流「盆石」,即白砂、鹅卵石和岩石排列在黑色漆盘上,以微缩的方式再现著名景观的小空间,这些有别于传统表现方式的大规模「盆石」,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
庭园的南端有四株樱花树,通向能剧舞台。始于14世纪的能剧,是将舞蹈、音乐和话剧融为一体的日本古典艺术的典范,也是世上现存最古老的歌舞表演艺术形式之一。细川忠利的祖父细川藤孝是藩祖,也是一位活跃的能乐鼓手,所有细川家族成员因此都成为了能剧的热心支持者。这座剧场初建于1878年,1965年被焚毁,现在的剧场是为纪念昭和天皇在位60周年,于1986年由旧八代城主松井家搬迁至此。在夏季的几个月里,这里会在松明火把的照耀下举行夜间能剧表演。
庭园的西端是拥有400年历史的茅葺屋顶建筑「古今传授之间」。在这里喝杯抹茶,俯瞰池塘,欣赏庭园美景,甚是惬意。
成趣园现为日本「国家指定名胜史迹」。

《豌豆黄》B0000000661 · 2024年8月3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小吊梨汤五角场万达店
豌豆黄,北京传统名点,与豆麺糕、艾窝窝、糖卷果、姜丝排叉、糖耳朵、麺茶、馓子麻花、蛤蟆吐蜜、焦圈、糖火烧、炒肝、奶油炸糕一起,并称「老北京小吃十三绝」。
豌豆黄的主要食材是豌豆。关于其做法,当代著名文学家、散文家、吃货汪曾祺在其美食散文《豌豆》有过描述:
「北京以豌豆制成的食品,最有名的是『豌豆黄』。这东西其实制法很简单,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5寸×3寸的长方块,再加刀割出四方小块,分而不离,以牙签扎取而食。据说这是『宫廷小吃』,过去是小饭铺里都卖的,很便宜,现在只仿膳这样的大餐馆里有了,而且卖得很贵。」
老北京的吃食有汉、满之分。汉即汉人吃食,满即满人吃食。豌豆黄最早是汉人民间小吃,据说有一天慈禧在北海静心斋歇凉,听闻大街上有挑担卖豌豆黄的吆喝声,便命人去买来尝鲜。慈禧尝过 之后,赞不绝口,豌豆黄由此上了御膳房的菜谱,成为汪曾祺所说的「宫廷小吃」。
宫廷吃食在选料和制作上肯定比民间吃食讲究了许多。所以豌豆黄有细、糙之分。宫廷的叫「细豌豆黄」,民间的叫「糙豌豆黄」。

《战国武士秀》F0200000068 · 2024年7月28日摄于日本熊本熊本城遗址
尽管在日本中世早期,靠自己奋斗而成功的军事人物的地位不断超过贵族,但贵族出身同样能在武士的世界中赢得一席之地。在室町时代和安土桃山时代的长年战乱中, 拥有贵族血统的日本武士,往往在此间兴盛的松散地方武装部队中, 被任命为军官。
然而, 16世纪末兴起的军阀领主一般出身寒微,如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他们取得权力是靠着出众的战略才华和军事资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信长还是秀吉,他们从未得到将军的头衔。因为长久以来,这一头衔和代表着统治不力的贵族军人联系在一起,因而有负面含义,也许部分原因是他们低微的社会地位。

《战国武士秀》F0200000067 · 2024年7月28日摄于日本熊本熊本城遗址
到日本战国时代,在武士阶层内部,家臣已建立起了对领主牢不可破的忠诚。武士家臣根据早在7世纪到9世纪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思想的规范,为领主效忠,得到物质利益和无形的奖赏为报酬。作为回报,这些拥有土地的家臣有义务为他们的主公尽忠,如地方领主,或者后来江户时代的将军。家臣或武士期望得到实实在在的报酬,比如土地或俸禄等。
其他人,如农民和雇农,在地方领主和军队官员的土地上耕种,以换取保护和生存权。步兵往往就从农民、雇农阶层中征召,虽然这些战士在交战中必不可少,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特权,俸给不多,社会地位低下, 并很少能在武士统治阶层中获得头衔。

《战国武士秀》F0200000066 · 2024年7月28日摄于日本熊本熊本城遗址
在和平年代,著名的武士道被仪式化了,最初,这看来并不协调。虽然德川幕府严密监管武士以防止战争和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江户时代的武士还是要遵行严格的道德规范,并要磨炼与其优越地位相称的武艺。另外,在德川幕府统治之下,武士的传统原则成为核心,而非军事经验。并且,即使在和平年代身兼政府管理职能,大名和武士也受到敦促,重视英勇、荣誉和责任。
在整个日本中世时期,武士等级制度一般效仿领主与家臣的关系网,这长久以来一直是日本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但是,在德川幕府的和平年代,这些特征却减少到了最低限度。江户时代将军重新分配了大片土地,地位和财富的分封,都是通过向将军效忠并证明自己的忠心而得到的,从而颠覆了几百年来的封建结构,甚而是更古老的贵族关系。

《战国武士秀》F0200000065 · 2024年7月28日摄于日本熊本熊本城遗址
在德川幕府统治开始的第20到30年间,为在江户统治者面前得蒙宠用并保证其地位所需的巨大花费, 进一步耗尽了武士日益减少的资源。1634年,德川幕府为武士及其家人设立参觐交代制,命令武士每隔一年要在首都的宅邸居住。一开始,幕府欢迎大名将其家人留在江户,从而使他们成为大名联手进攻都城时将军手上的人质。
很快,这一制度继续发展,藩国大名必须隔年觐见江户幕府,从而确保武士忙于两地奔波,没有时间、动力和资源来组织能够推翻德川政权的帮派。参觐交代制结合幕府统治的其他特点给武士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制度有助于疏离地方大名与其家臣和领地的关系,保证江户时代的幕府统治不会被地方的权力争夺所瓦解。尽管在某些场合,武士仍然可以佩带武器,但是参觐交代制和随之而来的长途旅行的负担,已使他们实际的俸给减少。 由于名目繁多的法令法规和各种赋税,包括城堡的兴建和维修,还有大名家族之间的联姻,武士的行为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
并且,幕府任用密探和视察员,确保武士遵从其法令。参觐交代制对财力雄厚的武士确有好处,因为富有的大名得以发展自己的人文爱好。幕府所培育的和平年代,促进了武士对闲暇消遣的投入,如戏剧、文学、音乐和其他娱乐形式。
最后,庞大武士群体的巨大消费推动了江户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繁荣的大都会,最终受益的,不仅是德川幕府,还有商人和手工艺者阶层。因此,德川幕府的统治使武士的社会地位和日常生活都发生了革命性剧变。很多武士被吸纳为幕府的行政官员,这类职位与平安时代朝廷鼎盛时期侍候于都城的侍臣相差无几。

《战国武士秀》F0200000064 · 2024年7月28日摄于日本熊本熊本城遗址
德川幕府在1615年正式统治日本,迎来了250多年的和平年代,并实施了锁国政策,使日本隔绝于异国贸易和纷争之外。武士不再忙于征战,因为德川幕府为维持秩序,对国内事务,尤其是对藩国,实行了严格的控制。 很快,很多武士成了幕府官员,在都城和偏远地区为幕府效力。还有一些武士的存在变得有名无实,只是定期礼节性地到江户觐见将军,代表领主向将军进贡。
因此,在日本江户时代, 武士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川统治者随意按照武士的忠诚度和自己的战略目标重新分配土地,阵前之勇无法再保障武士家族首领获得大名之位,家族派系也无法带来财富和威望。要上缴给将军的地产税和贡税的增加,甚至给高层大名造成了经济困难,他们也无法再依赖于恭顺的家臣武士体系了。

《战国武士秀》F0200000063 · 2024年7月28日摄于日本熊本熊本城遗址
起初,这类私人训练的武装力量稍显不正规,但是到镰仓末期,武士团变得组织有序,并构成了私人军队的主要力量。镰仓幕府为了应对来自这些武装的威胁,于1232年颁布新的法令来约束御家人的行为,期望能够加强地方秩序,通过荣誉和诚信机制来规范武士的行为。但是在江户时代武士法规正式出台之前,这些典范大多被武士阶层所忽视。满国纷争四起,武士挑战幕府的权威,争夺个人财产、土地和金钱,都称不上荣誉之战。
日本镰仓幕府最终在1333年垮台,足利家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室町幕府。在幕府政权的纷争中,相继出现了三个武士,他们对国家大权的争夺愈演愈烈,分别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这三人都致力于统一全国,但只有家康最终达成了这一目标、将日本统一在德川幕府的旗下。15、16世纪,在中央政权和社会秩序的一片混乱中,武士家臣受到这三位著名武士的影响,纷纷废黜了代表幕府的守护和地头,史称「下克上」,即下级推翻上级。

《战国武士秀》F0200000062 · 2024年7月28日摄于日本熊本熊本城遗址
从日本中世早期开始,地方武士团就是由领主与家臣关系联结而成的、各事其主的独立武士团体联盟。实际上,领主和家臣的盟约起到了联系双方纽带的作用,由此,家臣的后代为领主家族的后代效力,作为回报,领主一直为家臣提供俸给。尽管领主和家臣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常用暗示亲属关系的语言来说明并表达彼此间的关系。例如,家臣被称为「家人」或「自家儿女」。家臣有时也把领主描绘成父亲的形象,虽然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在13世纪和14世纪,幕府把从前只赏赐给贵族的封赏和财富赐予御家人,甚至在军事集团实力壮大时也是如此,这无意中加速了中央政权的瓦解。最初,统治者重用武士军队,因为他们有出色的军事头脑和稳固的地方关系或亲属关系,这些都是农民武装所缺乏的。但是,私人的关系使武士家臣更加委身于地方领主。 地位稳定的大名和御家人充分利用这种联盟,在远离都城的地方积聚大片土地,因为他们确信,武士军队能够保护藩国不受中央政府的干涉。

《战国武士秀》F0200000061 · 2024年7月28日摄于日本熊本熊本城遗址
在日本,军队早在中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例如,在日本奈良时代,政府军队由从藩国农村征召的农民构成。在中世早期, 从10世纪开始,日本政府强制征兵的制度开始松动。尽管朝廷努力建立国民军部队,但是, 最终贵族和皇室都得求助于地方武士群体来维持偏远地区的秩序,而中央统治者在那里几乎没有任何势力。
在12世纪,随着日本京都贵族朝廷的没落, 武士阶层开始在偏远地区崛起,之后他们的势力扩展到日本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 主导力量。武士在平安时代中后期迅速掌权,一部分原因是,京都贵族在其私人产业上纷纷雇用武士, 这一做法推动了武士的发展。
日本朝廷高级大臣们通常居住在日本的文化中心,根本无心也无力管理他们在藩国的大片土地,也就是称为庄园的私人产业。不但如此,他们反而请具备军事能力的个人做庄园的代理和管理者。由此,对这些土地的日常管理和防御就成为职业军人团队的职责,而贵族实际上并未参与其中。
这些自平安时代后期崛起的武士被称为「武士团」,所有这些准军事组织都由职业战土组成,因而与缺乏正规军事背景的政府征召的军队明显不同。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武士团居住在东部诸国,即关东地区。除了朝廷贵族以外,中央政府和贵族血统以外的私人地主也都 雇用武士团,其目的各有不同,如守卫都城或保护村庄等。 很快,武士就变得必不可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