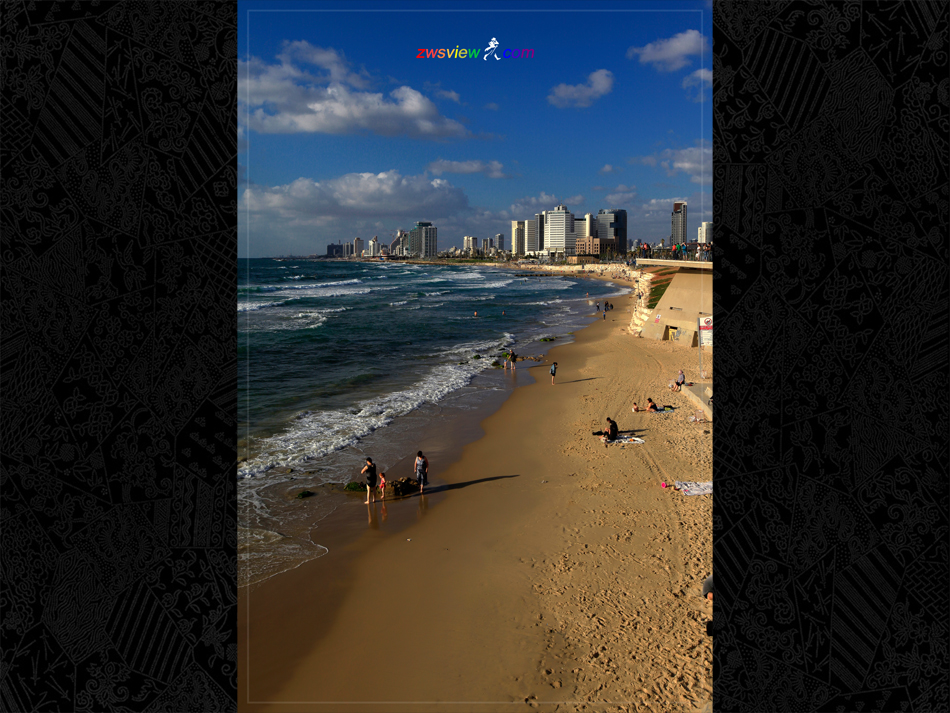《金字塔》A0501000008 · 2013年6月1日摄于埃及开罗
墓志铭,刻于墓碑或陵寝,是世人对后世最后的告白。
世界上最著名的墓志铭应该是镌刻在法老图坦卡蒙陵墓上的一段文字:「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段文字据说非常灵验,号称「法老的诅咒」。此事在「印象埃及」中有说,不再赘述。
并不是所有的墓志铭都这般威严。近日看到这样一样墓志铭,笑到喷饭:
「初从文,三年不中;改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又从商,一遇骗,二遇盗,三遇匪;遂躬耕,一岁大旱,一岁大涝,一岁飞蝗;乃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此翁文不成,武不成,商不成,农不成。最后学医倒是有点眉目,只可惜不知出了什么状况,把自己给药死了。
据说此文出自明清笑话集《笑林广记》的《杨一笑传》,但《笑林广记》并无此文,应该是今人编的段子。有好事者意犹未尽,续了一个「加强版」:
「初从文,三年不中;改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又从商,一遇骗,二遇盗,三遇匪;遂躬耕,一岁大旱,一岁大涝,一岁飞蝗;乃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遂至地府,久候阎王升堂,不耐,问之,鬼卒曰:王阅足下卷宗,狂笑,休克于后堂,未醒。」
此翁嘎屁后,跑到阴曹地府,干等半天就是不见阎王。问小鬼,阎王在干嘛,为什么迟迟不露面。小鬼道出了实情。原来阎王爷看了此翁的生平事迹,严重笑晕,醒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