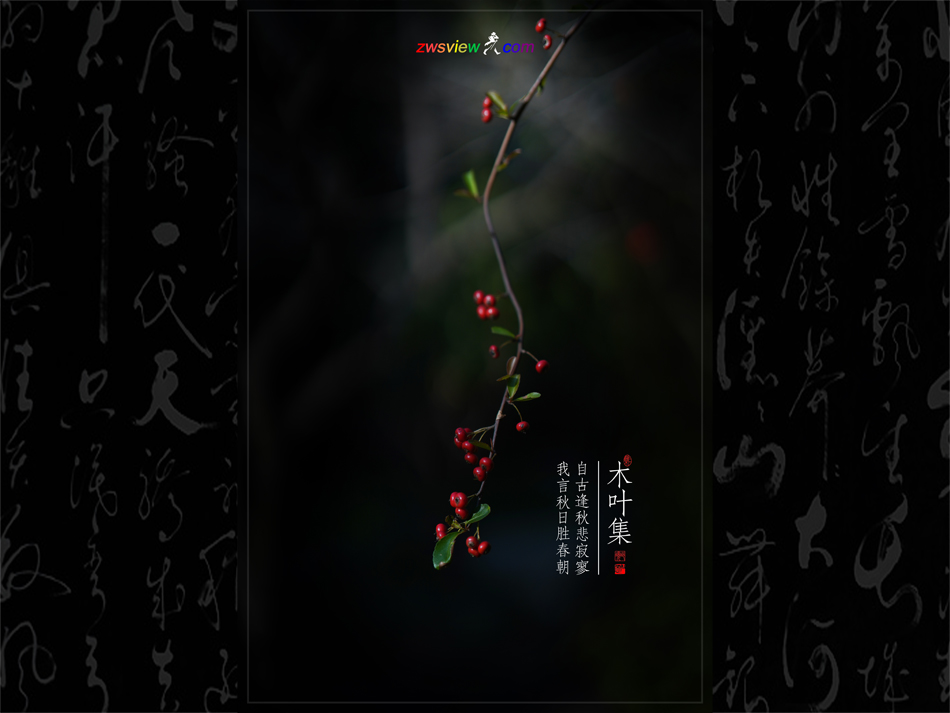《果木烤鸭》B0000000322 · 2022年8月18日摄于中国上海宝山黛瓦宴
《烤鸭》
梁实秋
北平烤鸭,名闻中外,在北平不叫烤鸭,叫烧鸭,或烧鸭子,在口语中加一子字。《北平风俗杂咏》严辰《忆京都词》十一首,第五首云《忆京都 · 填鸭冠寰中》:
烂煮登盘肥且美,加之炮烙制尤工。
此间亦有呼名鸭,骨瘦如柴空打杀。
严辰是浙人,对于北平填鸭之倾倒,可谓情见乎词。
北平苦旱,不是产鸭盛地,惟近在咫尺之通州得运河之便,渠塘交错,特宜畜鸭。佳种皆纯白,野鸭花鸭则非上选。
鸭自通州运到北平,仍需施以填肥手续。以高粱及其他饲料揉搓成圆条状,较一般香肠热狗为粗,长约四寸许。通州的鸭子师傅抓过一只鸭来,夹在两条腿间,使不得动,用手掰开鸭嘴。以粗长的一根根的食料蘸着水硬行塞入。鸭子要叫都叫不出声,只有眨巴眼的分儿。塞进口中之后,用手紧紧的往下捋鸭的脖子,硬把那一根根的东西挤送到鸭的胃里。
填进几个之后,眼看着再填就要撑破肚皮,这才松手,把鸭关进一间不见天日的小棚子里。几十百只鸭关在一起,像沙丁鱼,绝无活动余地,只是尽量给予水喝。这样关了若干天,天天扯出来填,非肥不可,故名填鸭。一来鸭子品种好,二来师傅手艺高,所以填鸭为北平所独有。抗战时期在后方有一家餐馆试行填鸭,三分之一死去,没死的虽非骨瘦如柴,也并不很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鸭一定要肥,肥才嫩。
北平烧鸭,除了专门卖鸭的餐馆如全聚德之外,是由便宜坊(即酱肘子铺)发售的。在馆子里亦可吃烤鸭,例如在福全馆宴客,就可以叫右边邻近的一家便宜坊送了过来。自从宜外的老便宜坊关张以后,要以东城的金鱼胡同口的宝华春为后起之秀,楼下门市,楼上小楼一角最是吃烧鸭的好地方。在家里打一个电话,宝华春就会派一个小利巴,用保温的铅铁桶送来一只才出炉的烧鸭,油淋淋的,烫手热的。附带着他还管代蒸荷叶饼葱酱之类。他在席旁小桌上当众片鸭,手艺不错,讲究片得薄,每一片有皮有油有肉,随后一盘瘦肉,最后是鸭头鸭尖,大功告成。主人高兴,赏钱两吊,小利巴欢天喜地称谢而去。
填鸭费工费料,后来一般餐馆几乎都卖烧鸭,叫做叉烧烤鸭,连闷炉的设备也省了,就地一堆炭火一根铁叉就能应市。同时用的是未经填肥的普通鸭子,吹凸了鸭皮晾干一烤,也能烤得焦黄迸脆。但是除了皮就是肉,没有黄油,味道当然差得多。有人到北平吃烤鸭,归来盛道其美,我问他好在哪里,他说:「有皮,有肉,没有油。」我告诉他:「你还没有吃过北平烤鸭。」
所谓一鸭三吃,那是广告噱头。在北平吃烧鸭,照例有一碗滴出来的油,有一副鸭架装。鸭油可以蒸蛋羹,鸭架装可以熬白菜,也可以煮汤打卤。馆子里的鸭架装熬白菜,可能是预先煮好的大锅菜,稀汤洮水,索然寡味。会吃的人要把整个的架装带回家里去煮。这一锅汤,若是加口蘑(不是冬菇,不是香蕈)打卤,卤上再加一勺炸花椒油,吃打卤面,其味之美无与伦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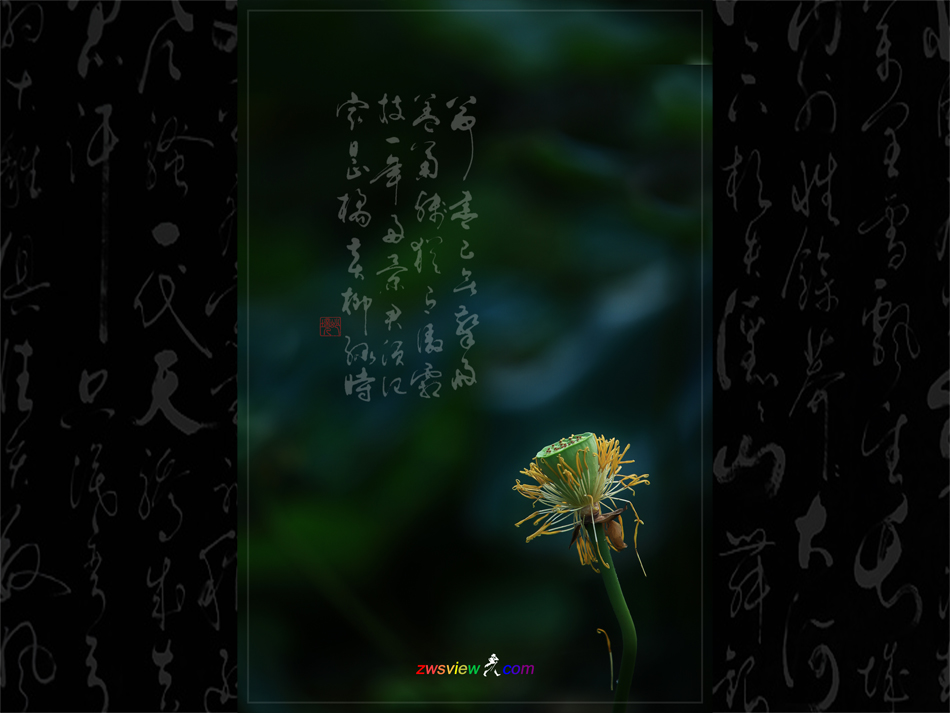
《荷趣》D0002000008 · 2011年7月2日摄于中国上海嘉定
《夏天》
汪曾祺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人们往往把栀子花和白兰花相比。苏州姑娘串街卖花,娇声叫卖:「栀子花!白兰花!」白兰花花朵半开,娇娇嫩嫩,如象牙白色,香气文静,但有点甜俗,为上海长三堂子的「倌人」所喜,因为听说白兰花要到夜间枕上才格外地香。我觉得红「倌人」的枕上之花,不如船娘髻边花更为刺激。
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珠兰。
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
秋葵也命薄。瓣淡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
凤仙花有单瓣者,有重瓣者。重瓣者如小牡丹,凤仙花茎粗肥,湖南人用以腌「臭咸菜」,此吾乡所未有。
马齿苋、狗尾巴草、益母草,都长得非常旺盛。
淡竹叶开浅蓝色小花,如小蝴蝶,很好看。叶片微似竹叶而较柔软。
「万把钩」即苍耳。因为结的小果上有许多小钩,碰到它就会挂在衣服上,得小心摘去。所以孩子叫它「万把钩」。
我们那里有一种「巴根草」,贴地而去,是见缝扎根,一棵草蔓延开来,长了很多根,横的,竖的,一大片。而且非常顽强,拉扯不断。很小的孩子就会唱:
巴根草,
绿茵茵,
唱个唱,
把狗听。
最讨厌的是「臭芝麻」。掏蟋蟀、捉金铃子,常常沾了一裤腿。其臭无比,很难除净。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天下皆重「黑籽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东墩产者最佳。
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刨去皮,则瓜肉浓绿,籽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虾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虾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蝈蝈,我的家乡叫做「叫蚰子」。叫蚰子有两种。一种叫「侉叫蚰子」。那真是「侉」,跟一个叫驴子似的,叫起来「咶咶咶咶」很吵人。喂它一点辣椒,更吵得厉害。一种叫「秋叫蚰子」,全身碧绿如玻璃翠,小巧玲珑,鸣声亦柔细。
别出声,金铃子在小玻璃盒子里爬哪!它停下来,吃两口食:鸭梨切成小骰子块。于是它叫了「丁铃铃铃」。
乘凉。
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看月华。月华五色晶莹,变幻不定,非常好看。月亮周围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大圆圈,谓之「风圈」,近几天会刮风。「乌猪子过江了」:黑云漫过天河,要下大雨。
一直到露水下来,竹床子的栏杆都湿了,才回去,这时已经很困了,才沾藤枕(我们那里夏天都枕藤枕或漆枕),已入梦乡。
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过去了。

《冬》A0101040023 · 2020年1月1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江湾湿地
《友邦惊诧论》
鲁迅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炸猪排定食》B0000000312 · 2022年1月13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无印良品悠迈广场店
《五味》
汪曾祺
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调羹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别处过春节,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在山西人是大事。
山西人还爱吃酸菜,雁北尤甚。什么都拿来酸,除了萝卜白菜,还包括杨树叶子、榆树钱儿。有人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先问,那家有几口酸菜缸。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
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
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
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我和贾平凹在南宁,不爱吃招待所的饭,到外面瞎吃。平凹一进门,就叫:「老友面!」「老友面」者,酸笋肉丝氽汤下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作:「老友」。
傣族人也爱吃酸。酸笋炖鸡是名菜。
延庆山里夏天爱吃酸饭。把好好的饭焐酸了,用井拔凉水一和,呼呼地就下去了三碗。
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
四川夹沙肉用大片肥猪肉夹了洗沙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猪肉夹芋泥蒸,都极甜,很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
广东人爱吃甜食。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卖芝麻糊、绿豆沙,广东同学趋之若鹜。「番薯糖水」即用白薯切块熬的汤,这有什么好喝的呢?广东同学曰:「好!」
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我家曾有老保姆,正定乡下人,六十多岁了。她还有个婆婆,八十几了。她有一次要回乡探亲,临行称了两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白糖水。
北京人很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了。菜农也有种的了。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价颇昂。
北京人过去不吃蕹菜,不吃木耳菜,近年也有人爱吃了。
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
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由此可见,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
北方人初春吃苣荬菜。苣荬菜分甜荬、苦荬,苦荬相当的苦。
有一个贵州的年轻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的妈妈不远迢迢给她寄来一包东西,是「择耳根」,或名「则尔根」,即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
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务。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剧团到上海演出,他帮助搞伙食,这下好,不会缺辣椒吃。原以为上海辣椒不好买,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一家专卖各种辣椒的铺子。上海人有一些是能吃辣的。
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之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我吃过最辣的辣椒是在越南。一九四七年,由越南转道往上海,在海防街头吃牛肉粉,牛肉极嫩,汤极鲜,辣椒极辣,一碗汤粉,放三四丝辣椒就辣得不行。这种辣椒的颜色是橘黄色的。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涮,就辣得不得了。云南佧佤族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与川北吊在灶上的辣椒大概不相上下。
四川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是辣且麻,搁很多花椒。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大书三个字:麻辣烫。麻婆豆腐、干煸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不行。花椒得是川椒,捣碎,菜做好了,最后再放。
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了的咸菜和咸极了的咸鱼,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倒酱油。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与个人的性格习惯也有关。湖北菜并不咸,但闻一多先生却嫌云南蒙自的菜太淡。
中国人过去对吃盐很讲究,如桃花盐、水晶盐,「吴盐胜雪」,现在则全国都吃再制精盐。只有四川人腌咸菜还坚持用自贡产的井盐。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的人爱吃臭。
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卖油炸臭豆腐干。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而出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化大革命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
最高指示
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我们一个同志到南京出差,他的爱人是南京人,嘱咐他带一点臭豆腐干回来。他千方百计,居然办到了。带到火车上,引起一车厢的人强烈抗议。
除豆腐干外,面筋、百叶即千张皆可臭。蔬菜里的莴苣、冬瓜、豇豆皆可臭。冬笋的老根咬不动,切下来随手就扔进臭坛子里。我们那里很多人家都有个臭坛子,一坛子「臭卤」。腌芥菜挤下的汁放几天即成「臭卤」。臭物中最特殊的是臭苋菜杆。苋菜长老了,主茎可粗如拇指,高三四尺,截成二寸许小段,入臭坛。臭熟后,外皮是硬的,里面的芯成果冻状。噙住一头,一吸,芯肉即入口中。这是佐粥的无上妙品。我们那里叫作“苋菜秸子”,湖南人谓之「苋菜咕」,因为吸起来「咕」的一声。
北京人说的臭豆腐指臭豆腐乳。过去是小贩沿街叫卖的:「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臭豆腐就贴饼子,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汤,好饭!现在王致和的臭豆腐用很大的玻璃方瓶装,很不方便,一瓶一百块,得很长时间才能吃完,而且卖得很贵,成了奢侈品。我很希望这种包装能改进,一器装五块足矣。
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气死」即干酪,洋人多闻之掩鼻,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
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

《柴爿馄饨》F0300000482 · 2015年2月19日摄于中国江苏浙江绍兴安昌古镇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离休教授,著名作家,中国新诗界泰斗,同时也是一位美食家。今年一月,九十高龄的谢冕出版了他的美食散文集《觅食记》。《馄饨记柔》为其中的一篇。
文未读过半,涎已垂三尺。
《馄饨记柔》
谢冕
中国面食中除了面条是可汤可干的吃法外,全程和汤而吃的,可能唯有馄饨。带汤吃馄饨是常态,也有油炸着吃的,那是偶见。所以,说馄饨不能不说馄饨的汤,那是鱼水不可分的。鱼因水而活,馄饨因汤而活。馄饨在四川叫抄手,红油抄手是成都街头一绝,汤汁是红通通、火辣辣的,辣椒油、花椒油、胡椒面,全来。但是,四川抄手的底汤是鸡汤和猪骨熬制,却是不假。那年在成都,晨起遛街,商铺未开张,但店家早已收拾好几只鸡,熬汤待用。因为是亲眼所见,所以相信四川抄手的鸡汤是真货。但是成都以外,号称鸡汤的,真伪就难辨了。大体而言,总是代以味精、香醋诸物搪塞。
馄饨是面食中的小家碧玉, 用得上一个「细」字来形容。它的特点是体积小,细弱的小,不似饺子馒头的大格局。印象最深的是八十年代在厦门鼓浪屿轮渡码头,有当地妇女街边用担挑小炉灶现煮小馄饨。当时一元钱可买一百只小馄饨,摊主用手拨拉计数,一五一十,极其精细。那馄饨小如林间落花,浮沉水中,鲜虾肉馅,白中透出红晕,美不 可言。一元钱可数一百只,每只一分钱,其小可知。论及性价比,放在今天,当然是不可思议的。重要的是那份小巧精致,来自闽南女性柔弱之手,绝对是巧手细活,世所罕见。别说价钱便宜,那份精致,喻为绝响,亦不为过。
在北京吃馄饨,有叫百年老字号的,位于京城某繁华区,平日门庭若市。我曾慕名前往。紫菜虾皮香菜为汤,稀汤寡水,皮厚馅小,状如煮饺,确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数十年居京师,总共只问津一次,不想再去。倒是有一年在海淀黄庄,偶见新开小铺,专卖馄饨,去了多次还想去。那馄饨包成圆形,薄而透明的馄饨皮裹着,汤中散开,状若一朵朵绣球花,极美。细查,发现不似是包捏的,更像是薄皮如丝粘裹而成的,可见其制作之精细。记得那小铺取名「黄鹤楼」,也许竟是来自江汉平原的店家?可惜却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而我总是惦记着。
馄饨在福建多地叫扁肉。特别有名的沙县小吃中,我每次总是点扁肉加拌面,二者是鸳鸯搭档,可谓绝配。沙县的拌面加碱,韧而柔,主要是拌料特殊,用的是花生酱。拌料置底,捞出的热面置上,另撒葱花于上,顾客自行搅拌。至于扁肉,一般馄饨肉馅是切肉或剁肉,而以沙县为代表的扁肉是打肉,即用木槌在墩板上不断敲打成肉泥。这样的肉馅口感特殊,柔韧之中有一种脆感。更重要的是它的汤清澈见底,上面漂着青绿的葱花,清而雅。一盘拌面、一碗馄饨,堪称世上最佳。
在我的家乡福州,扁肉的称呼又多了个「燕」字,叫扁肉燕。这主要是因为它的面皮用料特别,面粉、薯粉加上猪瘦肉,也是人工拚力敲打,摊成透明的薄皮,而后切成菱形小块,再包肉馅。因为扁肉燕的燕皮也是肉制品,谐称「肉包肉」。扁肉燕的馅除了精选鲜肉,必不可少的是捣碎的虾干,以及芹菜碎末和荸荠丁,鲜脆,味道是综合的,很特殊。扁肉燕名字雅致,也许是状如飞燕,也许是「宴」的谐音,它是福州的一张饮食名片,代表着闽都悠久的文化。
馄饨在广东叫云吞,这名字也很雅,云吞者,云吞月,云遮月之谓也。记得郭沫若当年曾为厦门南普陀素斋一道菜取名「半月沉江」,成为文坛佳话。可见菜名中也应有诗,菜因诗得名,也因诗而远播。「半月沉江」是,「云吞月」也是。粤菜的精致华美堪居举国之首,其他各菜系虽各有其长,但只能列名于后。而云吞是不曾列名于粤菜中的,云吞充其量不过是一道小吃而已。但广东的云吞实在不可小觑。至少在我,宁可不吃粤菜的烤乳猪、烧 鹅仔,也不会轻易放弃一碗三鲜馄饨面。
有一段时间我在香港做研究,住在湾仔半山区。我总找机会步行下山,在铜锣湾街头找一家馄饨店坐下来,美美地吃一碗地道的三鲜馄饨面。吃着吃着就上了瘾,以后总找借口一再问津。从湾仔、铜锣湾,一直吃到油麻地、旺角,甚至是尖沙咀的小巷,我都能找到我情有独钟的馄饨面。我发现所有的小铺都能煮就一碗让人忍不住叫好的、地道的馄饨面:细长又柔韧的碱面,清汤,虾仁鲜肉和菜蔬,最让人迷恋的是馄饨馅中竟然包着一只鲜脆的大虾仁。
香港商家不欺客。几乎所有的店家,只要是做鲜虾馄饨的,都包着这样的大虾仁,不变样。前些 日子重访香港,住在旺角,还是「怀旧」,特意过海找到我常常光顾的那家铜锣湾小店。人多,在门外排队,领号进门。食客几乎都是当地街区的居民,他们不仅是回头客,而且是常客。与之攀谈,均对小铺的馄饨赞不绝口:本色,地道,价钱公道。从沙县扁肉到香港馄饨,从火辣辣的龙抄手到家乡福州温情的扁肉燕,这道貌不惊人的中国面食,因为它的小巧玲珑,因为它的「美貌如花」,吸引了多少人的念想和期盼!
史载,早先的馄饨和水饺是不分的,二者的区分是在唐朝。「独立」之后的馄饨,自动走更加细腻精巧的路线,而与水饺判然有别:水饺逐渐成为一种主食,而馄饨依旧是茶余饭后的「随从」。在中国南部,皖南那边还保留了二者不分的「混沌」状态,那里的水饺是带汤吃的,近似馄饨的吃法。远近闻名的上海菜肉馄饨,不仅个头大得惊人,简直就是一盆带汤的饺子!一贯精细小巧的上海人,为什么会欣赏这个傻大粗的菜肉馄饨?摇头,不可解。

《老物件》C0000000040 · 2022年6月7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
《存在的理由》
林清玄
每到一个地方,我总会捡一些当地的石头回来作纪念,有些朋友无法理解,会问我:「石头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石头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它是一个地方最好的纪念,是金钱也不能买到的。」我说。
在我们的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一个石头、一朵野花、一株小草都是在诉说自己的价值,只是有缘的人才能看见罢了。
一个黑色的石头可能比一张鲜红的缎子更明亮。
一件母亲缝制的粗布衣裳,却比闪闪发亮的新衣更温暖。
一棵林间的小树,有时比娇贵的兰花更令人动容。甚至连每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吧!有些为爱存在,有些为学习存在,有些为生命的美好而存在。只有一个人确定了自我存在的理由,才可能成为更自信、更深情、更温柔的人。

《龙舟》A0104060002 · 2011年4月5日摄于中国江苏兴化
《端午日》
沈从文
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节,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作起点,税关前作终点,作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各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嘭嘭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凡是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
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派士兵把30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
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上海国际时尚中心》A0101040015 · 2014年2月23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
《药》
鲁迅
一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窸窸窣窣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静下去,才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你娘会安排的。」
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门,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天气比屋子里冷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
「哼,老头子。」
「倒高兴。」
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太陽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 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但是没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老栓见这样子,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他的女人,从灶下急急走出,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
「得了么?」
「得了。」
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商量了一会,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小栓也吃完饭,他的母亲慌忙说:「小栓,你坐着,不要到这里来。」一面整顿了灶火,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们吃什么点心呀?」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此时恰恰蹩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便坐下问话,然而没有人答应他。「炒米粥么?」仍然没有人应。老栓匆匆走出,给他泡上茶。
「小栓进来罢!」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
「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工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上注进 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
「睡一会罢,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三
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你生病么?」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
「没有。」
「没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 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里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肚饿?」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劳里,还要劝劳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
「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四
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微风起来,吹动他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跄跄踉踉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华大妈见这样子,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他说,「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人点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声吃吃的说道,「你看,看这是什么呢?」
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的说,「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 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过年》C0000000035 · 2022年1月16日摄于中国上海长宁
《过年》
鲁迅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
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